
必然的悲傷跟意外的悲傷是有差別的,
差別在於遺憾的程度。
是遺憾讓我們念念不忘,
是遺憾讓我們難以釋懷。
人生中幾次面對死亡的經驗都帶給我不同的體會,第一次,是七歲時父親的驟世。因為年紀還太小,隱隱約約知道是一個人不會再回來,卻碰觸不到悲傷的深處。幾個畫面在腦中的記憶還存檔著,是父親入殮時帶著刀痕的面容,奶奶與母親失魂哀淒的神情。盛大的喪禮,白髮人送黑髮人,寡母領著孤兒,眾目睽睽。
七歲的我自然無法共情於大人們,需要經過很久很久以後,被社會打磨幾年,也與他人建立起足夠深厚的感情,才能稍微明白失去的悲傷,也才能真正意識到,當初父親被人砍殺的意外是如何巨大的震撼,足以摧毀家族所有大人們的信仰。
時間轉眼來到28歲那年,再此之前,我已經陸續送走了外婆、外公、爺爺、奶奶。一代人的消退,是另一代人取而代之的必然過程。也是同年,我失去了人生中真正意義上的父輩,我的四叔,父親最小的弟弟。正值壯年的他被診斷出肺癌末期,治療不滿12個月便辭世,時年48歲。四叔走前一個月,奶奶過世,接連舉辦兩場喪禮,令家族裡所有人都身心俱疲。
四叔在的時候,我並不覺得他是我生命中一個特殊的存在。他是長輩,未娶妻前跟自己的父母、姊姊、大哥的遺孀住在一起,這在大家族的環境中是很常見的情況。奶奶有7個孩子,四叔排行老七,據她說自從四叔開始工作後,每年除夕夜都會買一顆日本進口的蘋果連同紅包給她。準時在午夜十二點出現,陪她吃完那顆蘋果才會離開。
但這麼一個孝順的么兒,卻在終身大事上做了最大的忤逆。我的四叔娶了一位當時爺爺奶奶都不認可的女孩做老婆,婚宴在他們的新家舉行,雙方父母都缺席,只有親近的家人朋友出席,是當時才國小五年級的我,參加過的最簡陋的一場婚宴。

人生中很多事情,在發生的當下你並不覺得會對往後的你帶來什麼影響,直到我開始戀愛,也涉及到結婚這件事時,才驚覺深植心中那股逆反的性格從何而來。比起迎合父母,選擇自身所愛才更加重要。我常想,同樣身為女人,四嬸嬸是幸運且幸福的,一個男人不用為妳對抗全世界,只要為妳對抗全家人就好。
婚後,四叔依然經常回家見父母,是所有娶妻之後的叔輩中,最常回家的一位。帶著那位他不受待見的妻子,克盡為人子女的責任。婚前的四叔對待我跟大妹妹十分嚴厲,唯獨寵愛小妹妹,似自己的女兒那般的疼。這樣的愛直到他自己後來生兒育女也未曾改變過,我甚至覺得婚後的四叔變得更加溫柔可親,有什麼好吃好玩的絕對連帶給我們都配置。我們一家跟他家走的極親近,隨著堂妹堂弟的降臨,有過一段很長很長,其樂融融的日子。
畢業後我北上工作,只有逢年過節回屏東老家才會見到四叔。隨著我日漸成熟,才發現當初仰視的大人們都逐漸老去。我第一次有一種「自己未來的成就會超越他們的感覺」,原來,這便是一個孩子成為大人的瞬間。我跟四叔在台北見過一次面,那時他因公事北上處理工作,順道來上班的地點探視我。見我在當時台北最高的大樓上班,眼裡溢滿欣喜。我想,他一定覺得這個大姪女很有出息吧。

只是我從來沒想過,日後跟他相處最密集的時間會是他最後在病床上的那一週。2005年5月,奶奶過世,四叔住院,他們母子相互隱瞞自己的病情,隨後前後腳在黃泉相聚。這麼荒謬的劇情,就連最狗血的鄉土劇都不敢寫。原本請假回家奔喪的我,被家裡的大人派到病房陪伴四叔。他那時正在接受最嚴峻的治療,幾乎無法進食,只能仰賴鼻胃管。原本因中年稍稍發福的體態,只剩僅存的37公斤。
拖著殘破不堪的身體,在病榻上一息尚存的他仍不忘問我:「母親節準備帶奶奶去哪裡慶祝?要告訴她”我出差了”,不然她會起疑心。」
在醫院陪他的那一週我經常在半夜驚醒,總是要湊近確認他的鼻息後才能再躺回去。白天,若是他精神尚可,會跟我聊各種關於他的大哥我的父親的事蹟。那是他第一次主動提起自己的大哥,洋溢著年輕又帶點崇拜的語氣,說到激動處會展露我從未見過的笑容。我一方面覺得安慰,一方面又止不住擔心,恐懼於當他開始回憶,是否就表示他離時日無多越來越近?
若是如此,那我寧可不要聽那些關於他的大哥我的父親的任何故事。
喪假加上年假來到尾聲,回台北的那天我在病床旁跟他道別。簡單的四叔兩個字梗在喉嚨說不出口,喊出來時已經淚流滿面。我聲嘶力竭的哭著,一字一句說著要他堅持下去的話。在有記憶的成長歲月中,這是我首次向家人展示毫無遮掩的情緒,那麼赤裸而不顧一切,遠比我想像中還要痛。
四叔的喪禮結束在夏天剛要開始的時候,四嬸拉著年幼的堂妹堂弟在靈堂向大家鞠躬,又一次,寡母領著孤兒,眾目睽睽。自此之後的好多年,我再也沒有踏進四叔家中。在心中,我一直抗拒踏入那個已經沒有他存在的三層樓房裡,抗拒去面對屋裡哪怕是一點有別於他生前擺設的改變。
與其說令我感到悲傷的是死亡,不如說令我感到悲傷的其實是遺憾。是遺憾讓我念念不忘,是遺憾讓我難以釋懷。

大衛‧尹格曼的《生命的清單》裡寫著:「人的一生,要死去三次。第一次,當你的心跳停止,呼吸消逝,你在生物學上被宣告了死亡。第二次,當你下葬,人們穿著黑衣出席你的葬禮。他們宣告,你在這個社會上不復存在,你悄然離去。第三次,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,把你忘記。於是,你就真正地死去,整個宇宙都將不再和你有關。」
因此有人會這樣安慰:「只要你記得他,他就永遠活在你心裡。」卻忽視了生物性、社會性死亡所帶來的影響。永遠活在心中有多麼抽象,現實生活中失去那個人的悲傷就有多麼具象。我選擇不用抽象的說法來自我說服,而是用真真切切的遺憾來提醒自己。
生者與逝者之間必定是存在難以割捨的紐帶,才讓死亡起了作用。透過自己的痛,我意識到也許很早很早以前,就已經把四叔當做是自己的父輩,你得到很多來自於他的關愛,卻沒有機會好好回饋給他。之後,我試圖從回憶中梳理關於他的一切,每想起一個畫面、一件事,我就有再次與他靠近的感覺。直到真正確認「是的,他永遠活在我心中」時,面對要不要走進他曾經生活過的三層樓房裡這件事便再也沒有恐懼。
這一段靠近的過程我走了八年。八年後我踏入了四叔家,順著樓梯直通放著他的牌位的香案前,點了三支香,默默地望著相片裡年輕而俊朗的他。
這一回,我沒有哭。

不要逃避悲傷,
它雖然痛苦,
卻能真正讓我們堅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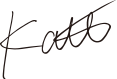
-凱特謎之音
【後記】
2020年,同樣是癌症,帶走了與我年紀相當的、最好的朋友。本以為來日方長,本以為可以相互看見彼此白髮蒼蒼,時間卻永遠靜止於她的43歲。餘下與我當年同樣年紀的七歲幼兒,我能體會她深深的遺憾與不甘。
經常想起她,也夢過她好多回。想起的回憶除了那些我們曾經經歷過的好時光,更多是她這個人帶給我的影響。有幾次,我甚至可以細細想起某一個夏天夜晚,在手機還未普及的年代,她打電話給我,我們一路聊到通宵的內容。那麼不愛煲電話粥的我,竟然意猶未盡。
不知道這次要花多久時間,才能走過那條從具象的悲傷邁向抽象情懷的路。但我知道,我一定、也能夠完成。






No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