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一直在追求自由,
卻也有甘願踏入圍城的那一刻。
坐辦公室的那八、九年裡,我換了五個公司。做的是設計工作,每跳一次槽,薪水就往上一階。我知道面試的主管為何喜歡用我,因為我能夠馬上接手,完全不需要適應與學習。但像我這種員工也是最無法掌握的,辦公桌永遠沒有私人用品,只有公司的東西,下班離開後,這個位子就像沒有人坐似的,嗅不出一絲主人的氣息。
我極討厭被規定上班時間,甚至打卡。一方面心高氣傲地認為設計工作就應該是彈性上班制,一方面是內心對體制深深的抵觸。年輕時眼裡沒有懼怕,以致於行為多半囂張。曾因為不按照公司上班的打卡規定被扣掉兩個月的年終,我也只是面無表情的從主管手上拿走那份通知。
幹設計沒有不私接案子的,以我25、26歲那會兒的狂妄,兩個月的年終,兩個禮拜的私活兒就能賺到了,用它來買自由,只是剛好而已。
自由是什麼?不是你想幹嘛就幹嘛,而是你不想幹嘛就不想幹嘛。自由,是說不的權利。
可是與此同時,我也知道自己終究不是自由之身。妹妹上大學的生活費由我負責,每個月需要往家裡給錢。很長的一段時間,我自由的基礎建立在不給自己製造更多負擔與牽掛。這種心態落實在生活上往往就變成:我不敢有任何可以眷戀的身外物。包含感情。
什麼斷捨離?什麼令人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術?哼,開什麼玩笑?從來就沒有這種困擾。
然而這一切的一切,與其說是補償,不如說是逃避。擁有說不的權利,獲得了片刻的自由, 卻怎麼看都好像從這一頭逃往那一頭,再從那一頭奔向另一頭。
30歲後迄今十幾年中,我如願以償做著自由度很高的工作。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,假期可以隨意調度,主要是這些工作的報酬還都不低,雖然忙起來是真的非常累,但比起上班,我還是喜歡這樣的工作模式多一點。很多人羨慕我,卻往往只看到美好的表面。真的要讓他們承擔相對應的代價,未必人人都扛得起。
一個曾經位居高管,卻因為體制內鬥爭而被迫離開工作崗位的朋友,自己成立工作室時已經37歲。他將近15年的工作生涯都在辦公室文化中,以致於剛創業那會兒,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安排日程。
「原來我的安全感竟來自於每天走固定的路去辦公室,以及每個月固定匯入帳戶的薪水數字。」 他苦笑著說。
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,有些人的自由不是行動不受約束,而是心中有一座需要他的城池。只要這座城不倒,就算被規定進出時間,他也覺得自己是自由的。
曾經有人問我:「既然享受自由,又何必結婚?」
這問題沒有標準答案,卻有一個既定的前提,也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婚後會變得不自由。但如同上述,有些人的自由並非建立在行為的不受約束,而是地位的重要性。某人和我,與其說給予彼此最大程度上的行為自由,不如說我們給予彼此最大程度上地位的重要性。所以即便結婚,從來也不曾覺得自己真的受制於什麼。甚至有時分隔兩地,也不覺得缺乏安全感。
五年前,在未與我做任何商量溝通之前,某人把一隻流浪貓從片場帶回家裡。他說:「這隻貓被買來拍片用,用完後被扔在片場。我現在收留牠了。」
我們大吵一架,我堅持把貓送走,他堅持非養不可。忽然間,我彷彿回到10幾年前那個不敢眷戀任何身外物的狀態,害怕生活多出一份意外與牽掛。
養奧斯托這五年中,心情是上上下下的。去年底她因為血壓升高再次壓迫到視神經而導致嚴重失明,從此便再也不能託付給親友臨時照看,主要是幾次拜託下來也覺得「誰都沒有我們照顧得細緻」。又老又病加上失明,安撫她的耐心可不能只有一點點。而無法離開家裡這個因素則大大限制了我與某人更多的活動自由,於是彼此商量,相互調配出差日期,並把家搬去了某人公司隔壁,讓生活之中隨時有人陪她,倘若外出超過5小時則有監控畫面可以隨時注意狀況。
新的住處稍稍遠離了市中心,心情上像搬到了一處與世隔絕的地方。從陽台落地窗面過去是一片毫無遮蔽的天空,方圓一公里以內,沒有比我們這棟樓更高的建築。偌大的三房兩廳只有一對夫妻一隻貓。
於是,我決定養些植物。
「妳不是害怕承擔生命嗎?這會兒養起植物,妳就更被困在這個家了。」某人說。
「我已經被困住了,就不差這幾棵樹啊花啊草啊什麼的了。」我說。
看一眼這屋,裡裡外外都是從前最排斥的身外物,從傢俱到寵物到植物到人。
錢鐘書老先生在自己的小說《圍城》裡這麼說過:「城裡的人想衝出來,城外的人想衝進去。但最後這座圍城就在這一矛盾中漸漸形成,這也正是生活的真諦所在,所以生活就像圍城。」
我的前半生一直在抵抗這樣的矛盾,最後卻還是心甘情願,將自己送了進去。

√ outfit of today
把這件網狀上衣穿得相對有個性一點是我的本意,但似乎不太受人待見。直男不知從何審美,直女覺得太過色情。
無法否認,有些衣服平胸穿起來更好看,尤其在這種時候。搭配一件質料稍微硬挺的下身,不管是裙子還是褲子,都有助於緩和網狀單品的曖昧不明。
唉呀,但我就是喜歡這種曖昧不明。
–
上衣/H&M,裙/self-portrait,墨鏡/ POLICE,包/SAINT LAURENT,鞋/PIERRE BALMAIN



圍城的含意很多樣,
用來解讀婚姻,
不過是因為普遍的人都有經驗罷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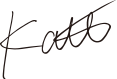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No Comments